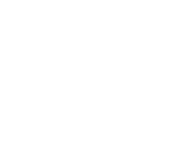“湖南有個蔡和森,湖北有個黃負生。”1922年,毛澤東在探望病重的黃負生時,曾如此評價兩湖地區(qū)革命宣傳隊伍中的佼佼者。蔡和森廣為人知,但知道黃負生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黃負生,原名鳳清,生于1891年8月,祖籍安徽休寧,父親到湖北做官,全家遷居武昌,于是他在武昌長大。他的母親是大家閨秀,通曉文墨,深明大義。在他父親早逝后,母親一邊做針線、紡織維持全家的生活,一邊教他誦讀詩書。家道中落,讓黃負生接觸到社會下層的生活,萌生了變革社會的想法。而受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為他探索社會變革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chǔ)。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爆發(fā),就讀于武昌曇華林工業(yè)傳習(xí)所的黃負生投筆從戎,以高度的熱情參加了革命軍,期望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但現(xiàn)實很快給他澆了一盆冷水。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見此情景,黃負生悲憤不已,他寫道:“漢家邊塞連烽火,楚國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已,中原從此不勝愁。”
革命不成功,黃負生并未意志消沉。據(jù)省博物館所藏其遺物看,1914年,他與漢陽漁家女王純素結(jié)為百年之好,當(dāng)時他在妻子的嫁妝鏡子背面寫詩:“天地山河/有情無情/皆能覺照本體/卻不留纖微塵影/這便是菩薩心”。詩中以鏡為喻,化用佛學(xué),表露出他向上的心境。婚后,他從事教育工作,繼續(xù)探索救國之路。
1915年,黃負生與“青年楷模”惲代英相識,他們召集同道,結(jié)成詩社,彼此唱和,互相砥礪。1916年,他創(chuàng)作《如是齋隨筆》,發(fā)表在《光華學(xué)報》上,他對有些青年浪費光陰而不能成就事業(yè)表示痛惜。他還從佛學(xué)中尋找救國救民的思路,認為佛學(xué)最重視的平等與博愛也是革命者應(yīng)有的精神。
1917年,黃負生到武昌中華大學(xué)任教,同時為了生活,也在漢口致忠中學(xué)、輔德中學(xué)兼課。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黃負生積極投身到這場愛國運動中。他與惲代英、林育南等在漢口華商跑馬場組織了萬人國民大會,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同時,他們還發(fā)動商人罷市,以壯聲勢。但在發(fā)動商人罷市時,軍閥政府不允許他們散發(fā)傳單。面對難題,黃負生提出“紙扇傳檄”的主意,即在紙扇上寫上“為了救國,全市商店罷市,此扇請傳觀”等字樣,以紙扇代替?zhèn)鲉危晒Φ貏裾f了武漢三鎮(zhèn)不少商家響應(yīng)義舉而罷市。
1920年,黃負生參加惲代英創(chuàng)辦的利群書社,不久就與朋友們一起創(chuàng)辦《武漢星期評論》,并任主編。他們深入調(diào)查工人的生活狀況,批判黑暗的現(xiàn)實。同年8月,根據(jù)調(diào)查的情況,黃負生和劉子通、陳潭秋一起撰寫了《漢口苦力狀況》一文,以“劉云生”為筆名,發(fā)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劉”即劉子通,“云”即陳潭秋(陳潭秋字云先),“生”即黃負生。文中稱:“漢口勞動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馱貨一類,人數(shù)既眾,生活尤難,疾病死亡,無人過問,自生自滅,若異類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實人生之難堪者。”下層民眾的苦難躍然紙上。
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黃負生在陳潭秋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11月,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漢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黃負生任宣傳委員。由于當(dāng)時大多數(shù)黨員是單身,只有黃負生已婚且有子女,便于掩護黨開展工作,所以經(jīng)過黨組織研究決定,由黃負生夫婦出面在武昌黃土坡租了一棟三層小樓,作為黨的機關(guān)駐地。在這個簡陋的樓房里,黨刊《武漢星期評論》編輯部、中國勞動組合會書記部武漢分部、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xué)說研究會等都在此辦公或開展活動。
作為宣傳委員的黃負生主要在學(xué)生和工人中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他改革教育,選用《新青年》等時文作教材,向?qū)W生宣傳馬列主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在省立湖北女子師范學(xué)校任教期間,他組織婦女讀書會活動,挑選青年骨干學(xué)習(xí)馬列主義著作,為日后的湖北女師學(xué)潮奠定了理論和組織基礎(chǔ)。他還在主編的《武漢星期評論》上致信讀者:“寧可為真理的犧牲者,不可為強力的征服者。”“教育前途,黑暗萬丈,要想將來放一線的光,全仗有覺悟的青年共同努力。”在上課之外,他在黨的機關(guān)駐地接待了大量來訪的工人。他發(fā)表時評《軍閥腳下底自治》,創(chuàng)作小說《夕陽會》《和平的死》,政治諷喻詩《湘鄂戰(zhàn)爭》,新詩《奴婢》《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聲》,呼吁社會關(guān)注、改變工人的悲慘生活。
黃負生既要在各個學(xué)校講課,為生活奔走,為黨組織籌集活動資金,又要忙于黨的宣傳工作,領(lǐng)導(dǎo)工人運動,他的身體在長時間的透支中,不幸患上了咯血癥,而這時又與執(zhí)教的中華大學(xué)當(dāng)局發(fā)生了沖突,最終導(dǎo)致他一病不起。當(dāng)時,《武漢星期評論》刊登了一封學(xué)生揭發(fā)中華大學(xué)當(dāng)局腐敗的來信,中華大學(xué)校長陳時得知此事后,在召開教職工會議時,說黃負生污蔑了學(xué)校名譽,要他交出投稿人的信息,黃負生斷然拒絕,表示要保護自由言論,并要求學(xué)校檢查自身的腐敗問題。最后,陳時命人將黃負生推出了會場。據(jù)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黃負生回到家后,與他和陳潭秋談到這場沖突時,“臉色由發(fā)青到發(fā)紅,一時咳嗽與氣喘發(fā)作起來,當(dāng)時即吐了幾口鮮血”。沖突發(fā)生后,中華大學(xué)解聘,湖北女子師范也不再續(xù)聘,患有咯血癥的黃負生臥床不起。后來,陳時聽聞黃負生病重,拿銀元到黃負生家慰問,被黃負生罵出。
1922年春,毛澤東為了揭露湖南軍閥鎮(zhèn)壓工人運動的惡行,在武漢中共黨的機關(guān),住了半個月左右,期間,他與病床上的黃負生有多次交談。同年4月,黃負生因醫(yī)治無效,病逝于武昌花園山仁濟醫(yī)院。遵照他的遺囑,陳潭秋、劉子通等將他安葬在武昌洪山獅子山。
1922年5月7日,上海《國民日報》的《覺悟》副刊刊登陳潭秋的悼念文章《負生底病——死》,文中說:“我們之中算負生思想最前進,最多能的了,他會詩能文,又演過戲劇,寫劇本,又寫論文又辦報……他死時,那么年輕,我們都非常可惜,說他是‘蛾子!蛾子!不飛不死!’”為了信仰,哪怕是死,也不能停止腳步,是對黃負生最中肯的評價。
(作者: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教師 介江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