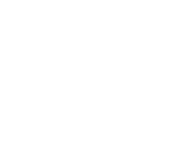本網評論員 金平
湖經之美,不僅體現在其“春花秋月”的自然景觀,更在于它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美的本質悄然融入教育的每個細節,創造了一種“平凡中見崇高”的審美實踐。
初入校園,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理性的詩意”。校園規劃未采用夸張的造型藝術,卻處處彰顯功能與形式的和諧統一。圖書館的玻璃幕墻不僅節能環保,更將自然光轉化為知識的隱喻;教學樓間的連廊不僅是交通紐帶,也成為思想碰撞的公共空間;學生公寓的布局既保障私密性,又促進社群互動。這種美不事張揚,卻暗合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的哲學理念——當建筑不再只是容器,而成為教育發生的“場所精神”,實用性與審美性便獲得了辯證統一。學校的物理空間告訴我們,大學之美首先應當是為“用”而設計,在滿足功能需求的基礎上自然生發出形式的美感。
學校的教學實踐體現了一種“務實的理想主義”美學。它拒絕將職業教育與人文素養對立起來,而是通過課程融合、校企協同、文化浸潤等路徑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這種跨界的教學智慧,打破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割裂,使專業技能培養獲得了人文視野的照亮。正如席勒在《美育書簡》中指出,只有當人“通過美從感性的人成為理性的人”,教育才真正完成其使命。學校的課堂不生產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是培養“完整的人”——既能勝任具體工作,又能反思工作意義;既掌握謀生技能,又理解生命價值。這種教育美學是對異化勞動的超越,是對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理念的當代詮釋。
在校園文化層面,學校培育了一種“活躍的沉思”氣質。學生社團既有貼近行業的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協會、農銀學社,也有追尋超越性的淺水文學社、米羅閣英語戲劇社;校園活動既有模擬求職大賽,也有青年微講壇活動。這種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構成了雅斯貝爾斯所說的“精神交往”的公共領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校的湯遜湖美育節,通過系列主題活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營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園文化氛圍。這種文化實踐既避免了后現代消費主義的淺薄狂歡,也跳出了保守主義的封閉自戀,展現出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可能路徑。
在這里,師生關系呈現出“親切的超越”特質。教授們沒有躲在學術高墻之后,而是在食堂與學生共進午餐討論問題,在創業基地手把手指導項目,甚至一起參加“彩虹跑”等活動。這種平等互動不是消解師道尊嚴,而是重建了孔子“浴乎沂,風乎舞雩”的教育情境。當知識傳授發生在生活場景中,當思想啟迪滲透在日常對話里,教育便從制度化的規訓變為生命間的相互喚醒。這種關系美學或許正是對現代大學“工具化”傾向的最佳矯正——它提醒我們,教育的本質不是生產標準化“產品”,而是在尊重每個生命獨特性的前提下,引導其朝向真善美的可能。
回望湖經之美,我們發現它實際上構建了一個“審美共同體”。這里的審美是師生共同創造、共同體驗的生活方式。從積思河畔的朗朗書聲,到實訓室中的專注側影;從運動場上的矯健身姿,到大活里的青春展演。湖經之美是AMAZING啦啦操隊在國際賽場上的閃光時刻,湖經之美是龍舟隊船槳激起的浪花,湖經之美是小慧哥哥跨越七年的愛心傳遞,湖經之美是校友孫雙雙在廣闊天地里的自強不息。這種美不依賴宏大敘事,而在日常實踐中確證著人的本質力量。它既是對康德“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呼應,更是對杜威“藝術即經驗”的實踐演繹。
湖北經濟學院或許沒有未名湖的浪漫傳說,沒有清華園的皇家氣派,但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回答了“大學何為”的根本命題。在功利主義肆虐的時代,它守護著教育作為“靈魂轉向藝術”的本真意義;在專業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它堅持培養“三有三實”人才的理想。這種美不事聲張卻深入人心,不尚浮華卻歷久彌新。
湖經之美啟示我們:教育的最高美學境界,莫過于讓每個平凡生命都能在實用與超越之間,找到自己詩意棲居的方式。